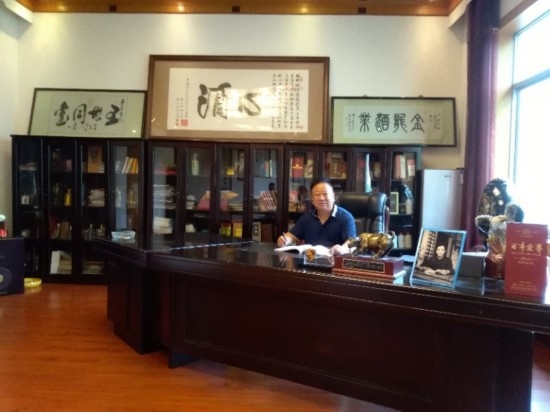1
母亲的生日,是农历三月初五。自从三十多年前离开家乡小村,每年这一天,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回来,家里像过节一样。
随着年龄增大,一年中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心中也想常回家看看,但最后都被一些“冠冕堂皇”的事务挤占了时间。转眼母亲已八十三岁了。
今年春节回家过年,已经感觉到母亲的苍老,雪白凌乱的头发,满脸粗糙的皱纹,步履已显蹒跚。过去精明能干的母亲,如今面对和面、蒸糕、包饺子这些年活儿,只能望洋兴叹了。我知道,母亲的未来日子越来越少,我尽孝的日子也正在与日递减。这样想着,一阵阵的惭愧,一浪高过一浪在心头涌动着。
二月下旬以后,父亲的电话曾一天两次打来,提醒我母亲的生日。其实我知道,这不是父亲主动打电话,而是母亲开始在家中唠叨了。
亲情的表现,有时不仅是衣食供给,还是一种温馨的陪伴。于是,我特意向单位办理了休假手续,网购了三月初二傍晚的高铁票,这次回家准备尽可能多陪伴父母一段时间。当晚我辗转回到家中,正如所料,父母都还没睡。二老坐在灯下等我,锅里还热着饭菜,床上新被套早已铺好。“我回来了!”游子一句简单的话,满屋子早已洋溢着无限亲情。
这就是家,一个不大但却给予我温暖的地方,从童年到少年,从小学到中学……我就从这里背起行囊,告别双亲,走出垄野,带着梦想奔向远方……
这就是家,小门,小院,篱笆墙,一切还都保留着我小时候的模样……唯一变化就是二十年前我种下的一丛幼竹,如今已经绵延一片,苍翠密集,绵绵蓄情。它们矗立于小院门前,为我守护着我的亲人和我曾经的岁月。
2
我的家乡小村,是以最先创村人的姓氏而命名为周家庄。传说祖上是兄弟二人,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;至我这辈,已达二十一世子孙,历经了四百余年发展,目前繁衍到几百户人家。
周家庄,离渤海南岸的羊口渔港码头,仅二十公里,因受海洋性气候影响,春夏时节,这里日夜温差较大。昨日返乡的疲劳,也让我自然美美地睡到清晨。我从庭树鸟鸣中醒来,闭着眼睛享受微寒的窗风轻轻抚面。小屋一人的世界里,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放松与坦然,好似外部的一切,离我那么遥远。“起床吧,饭都凉了”,母亲轻轻喊着我的乳名,就像稚童时的呼唤。睁开眼睛,母亲几乎贴着我的脸,慈祥地凝望着我,仿若在梦中。也许在我床头,母亲就这样慈祥地看着我,已经坐了很久很久了。
我努力回忆着母亲予我的最原始记忆,一点一点地向灵魂深处挖潜,脑际浮现出我二岁半时的难忘情景。一九七零年的夏天,妹妹刚刚出生,家里远亲近邻人都来看望,三姨提来一条刀鱼,看望哺乳期的母亲,大人笑着,说那鱼比我还高。
那时中国正处于物质极度贫乏的艰苦岁月,借着妹妹出生的喜庆,吃上些许美食,是最难以忘怀的事了。二岁半,对母亲当时的言谈举止,已经模糊不清。只记得,我呆在三姨怀里,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大人塞到嘴里的东西。如今,农村物质文化生活已丰富多彩,足不出户,一个电话打出,附近的酒店就会送来“量身定做”的美食,山珍海味摆满一案。虽说走南闯北,吃过了百家之饭;如今的我,仍然对家乡之食有种百吃不厌的偏爱。这方水土,养育了我,那种根植灵魂的故乡之情,也将陪伴我走过终生岁月。
3
清早起来,我搀着母亲,迎着朝霞,缓缓走出村外,信步于尺许高的青青麦浪之中,去感受这风情浓浓的乡野气息。昔日田间的沟渎池塘,如今早已干涸,遍布芦苇杂草。清风吹过,草木涌动出层层微波,恍若儿时的潺湲水流,汩汩欢笑。
渠沟两畔,杂樨荆棘半人之高。这是当年孩子们最喜欢的嬉戏迷藏场所。过去农村没有娱乐设施,这些荒坡野原沟沟洼洼就是孩子们的快乐自由的天堂。大家玩累了,"坏小子"就会商量些坏主意,或者去偷挖刚刚长包的蕃薯,或者翻墙偷摘农家尚未成熟的涩涩李桃。母亲边走边讲着我小时候的淘气事,在她老人家眼里,我依然是孩童模样。
返回村里,路过前邻三奶奶的院子。三奶奶已经作古,而院中那棵葡萄树依旧枝蔓茂盛。记得小的时候,在葡萄刚刚挂果的时节,三奶奶总是坐在葡萄架下严守看管。一见到我们这些探头探脑的小坏孩,她总会大声喝叱。而我们也总能趁她洗衣做饭的空档“迅速作案”,然后在惊恐慌乱中一哄而散。三奶奶的小脚从未能追赶上我们。每每如此调皮,顽童们却乐此不疲。
其实,三奶奶是位非常善良慈祥的老人。每年中秋时节葡萄成熟了,她都会采剪一些,分送邻里各家。品味三奶奶家酸中带甘的葡萄,也成为我童年难忘的记忆碎片。
一丝淡淡的乡愁总有母亲的影子,清贫的年代也有清贫的快乐,儿时的时间总是那么邈遥漫长。疯淘一天之后,天近傍晚,我就会坐在村头最高的地方,盼望参加集体劳动的母亲早些归来。那时我们小孩子的视野很小,眼中最大的世界就是母亲温馨的怀抱。
此刻,看着身边颤颤巍巍的老母亲,我把拉她的手握得更紧了。
4
几十年来,母亲对于自己的生日仪式并不看重,对于满案盛食似乎漠不关心。人情冷暖中,其实短暂陪伴才是亲情的价值所在,母亲欣慰的正是儿女的这点微薄孝情中透出的寸草之心。
然而母亲对于儿女的生日却格外寄重。小时候,即使家里日子过得再紧,生日这天,母亲都会给孩子煮上一只鸡蛋,并且看着我吃光,直到离开家乡。童年时代,独自吃完一个完整的煮蛋也就成为我的生日标志。记得父母对我祖上的生日也是敬重有加,不仅献上煮蛋,父亲还对祖上行跪拜大礼。今天,这些“繁文缛节”在我辈已经省略,我们仅仅献上“短暂陪伴”这一点点薄礼。
时光荏苒,我早已步入中年,但在我生日这天,母亲依然让父亲打来电话,嘱咐我吃一只鸡蛋,寓意一岁的圆满与顺利。
一种家风中洋溢出的幸福似乎在世世代代传递着。我的女儿渐渐长大,在她入大学之后的七八年里,我的生日里又增加了一个关爱我的人。生日这天,女儿带来的问候与祝福,让我感觉欣喜无限,我知道,一种孝道家风已经自然而然上下形成了。
其实人伦关系的纽带就是亲情!人间亲情是什么?是一杯递来的茶水,是一句简短的问候,是一双凝望的眼睛,是对坐无言的默契与依恋……而这些零零碎碎的互动与陪伴,恰恰蕴含着大爱无边。我常常问自己,家风,民风,国风,风是什么?风就是文化波动!文化到底是什么?文化其实就是一股道生之风,也就是在王道、国道、民道及家道中掀起的德行之风。国为国风,民为民风,家为家风,世为世风,而这股正气之风只能随着文化而波波无绝,代代延继。
浓春的家乡,夜风是清凉的,星星是灿烂的,亲情是温暖的。曾经躺在母亲怀抱中看到的月亮,如今依然挂在天穹,它弯弯的笑脸,似乎向我诉说着乡村的沧桑历史。
5
母亲生日正赶上谷雨时节,天地氤氲,竟然绵绵密密地飘下雨来。我仰着头,望着乌蒙的天空,任细雨清凉润面。阵阵东风吹得庭树摇来荡去,院中父母亲种下的几畦青菜,却尽情沐浴于甘露之中。
我家小屋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,显得古朴沧桑,并不明亮的老房灯下,父亲看着旧书,母亲静静地端着茶水,一只花猫安然睡在沙发的最深处。
小院南面的一棵古槐,两棵枣树,好似在我小时候就这般高,如今依然苍翠丰茂。据父亲讲,院中这棵老枣树他小时候就已很大,这样算来,已在我家历经百年风光了。
我的祖上应算诗书之家。祖父在民国时期正上师范时,恰逢日本侵华,祖父的老师带领包括祖父在内的大部分学生集体参加了国民军队,正面抗击侵略者,直到抗战胜利。祖父在世时,还经常给我们讲些他的生死经历,祖父九十三岁去逝,逝前留下了近十万字的回忆录。
受祖父国民党身份的影响,父母这一代在中国改革开放前,备受阶级成分的煎熬,我从小就能感受到家庭在村中的压抑。
1974年,我走进本村小学,记得母亲为我做的新书包都垂过了膝盖。在那个“唯成分论”的年代,上大学对于我们这些“五类分子”的后代而言是个永难实现的梦想。
6
到了母亲生日这天,清风徐徐,莺鸣传堂。一大早,村委两名干部就送来了喜庆的蛋糕,说了许多吉祥祝福的话儿。这是八十岁以上老人都享用的福利。这也是十九大以来,中央进一步惠民政策在乡村露出的春山一角。
记得小时候,村民吃不饱,还须向公社交爱国公粮。改革开放后的若干年里,“三提五统”的种种负担曾压得农民叫苦连天。十六大以后,国家废除了农业税费,后来进一步反过来实行种粮补贴。如今,国家全面精准扶贫,出台惠民政策,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国家将“为人民服务”由墙壁口号变成了现实,我所目睹的五十年乡村变迁,犹如纪实影片,历历在目。
母亲的生日宴在村南弥河北畔的一家酒店进行。菜品简单、朴素、惠用。没有豪奢之味,没有丝竹之乐,没有鞭炮之音。风声,雨声,祝福声,与天地苍茫邈邈浑然一体。酒店旁边这条弥河发源于临朐的沂山,在小村南面分叉两行,一条流向羊口码头,另一条流向东北方的大家洼镇老河口,正好将我的村子骑在中间。
我的初中就是在弥河西畔的西黑联中度过的,这家联中由附近的十几个村联合组成。1979年,我升入初中后,中国正经过“拨乱反正”,但教育秩序基本恢复正常,“成分论”已成过去。那时,母亲对我说的最多的话,就是鼓励我考取大学,向上发展。初中的三年光阴短暂而充实。中午住校,母亲会将家中最好的“干粮”放在我的书包里。这期间,我恶补着荒过的知识;其实我真正的人生一年级,是从初中正式开始的。十七岁那年,我考取大学,成为周家庄恢复高考以来的第一位本科生。
在我上大学离乡之后的三十三年里,每年我都经历双亲送儿离乡的一幕;年复一年,如今父母在村头招手离别的场景,已成为半百之我雕刻在内心深处的天地图腾。
7
人间美好的日子总是幸福而短暂,一周时光转瞬而逝。这段有亲情陪伴的日子里,每天都能听到父亲哼唱着小曲,母亲则欢快地进进出出,尽量将小院种植的劳动成果摆上案桌。
七天时光也是我一生中最轻松自在的日子。我走过田间垄头,跨越小沟小径,拨开荆棘丛杂,努力去觅寻记忆中那点点滴滴的痕迹。这个不大的村落,像一泓清塘,承载了我多少绵绵不绝的乡情。白云从树梢轻轻飘过,小鸟绕着屋顶环环飞翔,湾畔老槐树上花香四溢,静静的村落,就这么朴素、自然、恬逸。
从寒窗苦读到生存打拼,从一无所有至丰衣足食,从“少小离家”到“老大还归”,人生似一个圆,有时起点也就是终点。这样想着,一种生命沧桑感缓缓覆盖了忧忧的心田。多少次问自己,哪里才是我生命的真正归宿?是生命享受?抑或灵魂高尚的修养?
是荒塚暗居?抑或天堂大观的超然?
今天,我就要离开家乡了,济南的亲友已经来到小村接我。“娘,我得走了。”简单而低沉的告别。骨子里的我,从小就没有更多的蜜语甘言去安慰父母什么。
环顾温馨而又熟悉的小院,老屋,小门,枣树,翠竹,篱笆墙,还有茂茂密密的几畦青菜,还有庭台下大摇大摆的花猫,一切自然,亲切,安怡,令人依依不舍。
我走了,马达声告诉我,车子已经离开。我不忍心回顾父母苍老的身影,怕自己情不自禁地涌出泪水。我知道,父母一定还站在马路中间,一直缓缓地挥动着手,直到车后的烟尘慢慢散尽……
 手机版
手机版 |
阅读
|
阅读